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除法定节假日)
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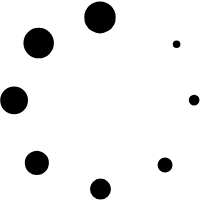
 2022-04-26
2022-04-26
恩格斯说过: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人类秉承着大自然给予的灵性,遵从着大自然固有的规则,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千百万年以后,渐渐地开始从大自然无数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在的世界。法律不外乎是人类社会秉承自然法、习惯法、道德律令以后,为了进行族群管理和社会控制而制订的一个新的社会规则。人类自从有了法律,就有了对法律的现实考量,更有了对法律的无尽无穷的哲学思考。尽管哲学家思维无法简单地取代法律思维。但哲学思维无疑对法律制度思维着无可置疑的引领和助推作用。哲学的睿思与邃密,哲学的广阔与深度,哲学的反思与批评,都是法律思维所必需的。如果说法律、法学、法律制度是一种力量,那么哲学思维就是一个方向。人们借助哲学思维的睿思和邃密、哲学的广阔与深度、哲学的反思与批评,就能够在法律之中发现问题、在法学之中分析问题,通过法学思考和讨论在法律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同样是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就意味着对于法律、法学、法律制度来说,同样一刻也不能没有哲学思维。
哲学的睿思和邃密、哲学的广阔与深度、哲学的反思与批评,对法律、法学、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够起着引领和助推的作用,就在于它促使人类必须时时思考: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到底派什么用场?法律到底应当怎样运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也许有一个很直观的答案:法律不外乎是人类用来进行更好的族群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手段,然而对于法律、法学和法律制度来说,有一个更为好听的说法是:为了给人类谋取幸福,为了实现人类的正义要求,给人类带来秩序。于是不管是为了解决民间纠纷、平息你争我斗、了断是非矛盾实现止争定纷,还是为了扬善惩恶、去残胜杀、以恶制恶、法律以各种形式和面目纷纷登场亮相。《尚书》有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汉书·刑法志》有云:“故胜任因天秩而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然而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历史和现实都很吊诡,需要事情应不应该是一回事,是不是又是一回事。法律当中的秩序与自由、正义与邪恶、利益与冲突、法治与人治、肯定与否定……总之这一切都归纳进了法学视野的同时,也进入了哲学视野。刑法史学者蔡枢衡谈到法的历史时说道:人类“有生活,就会有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对立的统一,也是一种肯定。有肯定,便会有否定。否定是统一的破裂,既有否定,便还会有否定的否定。否定的否定是对立统一破裂后的再统一,也是社会制度的重新肯定和高层次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制度-犯罪-刑罚,原来是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说明法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生活不断肯定与否定、相互转换和相互促进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对自己的价值目标、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不断肯定和否定,相互对抗和相互替代的历史,更有一部人类社会对自己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和价格目标不断进行深化认识的哲学思考史。
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在追求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秩序、文明……然而,野蛮往往与
文明齐头并进,而且让人类自身往往不解的是,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野蛮不断战胜了文明。每一次野蛮战胜文明,胜利者总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人类自身进行残酷的通知和野蛮的杀戮。于是野蛮和文明总是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相伴相生。检视历史有时真让人沮丧,但哲学却让人深思:野蛮和文明两者为什么靠得如此之近?两者为什么彼此不愿分离?两者为什么有时在同一个法律之中兼有并存?历史曾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使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是铁。恩格斯说过,冶铁术的发明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时代。但铁最初却是用来制造武器的。青铜器、铁的发明道理是用来铸犁还是铸剑的?铁究竟是文明的天使呢?还是战争的祸根?同样,法律的出现和存在,它到底给人类自身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法律到底是人类制度的“护花天使”还是野蛮残忍的“护身符”?马克思也说过,死刑不过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另一种支付令。也许野蛮与文明从来就是齐头并进的社会现象。所有这一切都值得、也必须进行哲学的思考才能让人看得更清楚。法律的文明和野蛮不在于它们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们的内在的本质内容。所以希特勒灭杀整个犹太民族的过程中,还出现和存在着大量隐性的“灭犹”法令。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有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正如有史学家所说的:“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但好在即使野蛮肆无忌惮的时候,文明还是顽强作出它应有的抗争。历史上无数的哲人不断发出呐喊:“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重新检视人类社会规则的发展际遇,社会的生存状况必须要有法律规则的约束,而法律规则的制定和运行,必须要有法学和哲学的支撑。法学与哲学天生也许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配偶。所以人类社会产生了不可胜数的法哲思想。哲学是关于世界的最根本性的学问,法学可以通过哲学的睿思和邃密、哲学的广阔和深度,哲学的反思与批评战线其治世和理民的规则统一性。哲学也可以通过法学体现其宏观知识的普通价值。哲学是聪明人的询问,法学是权利人的询问,法律曾是权利人的工具。在历史的各个时代和阶段。智慧者就像夜空中熠熠生辉的行星,照耀着人类的夜空。如果智慧者与善者相结合,这个世界就有希望;然而当指挥者与恶者相勾结,这个世界就会绝望。晚霞消失的时候,黑暗就会到来,以至黄宗羲有言:三代以上,法为天下之法;三代以下,法为一家之法,于是家法转化为国法。一旦私法与公法同质混同,公器就会转为私器,其结果神器必然沦为鬼器,执法就是镇压,成了一种治世的不二做派。好在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单轨式地发展前行的,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多元并列依存的共生关系,使人们不断认识到野蛮制度和残忍统治给人类甚至通统治者自身带来的伤害。于是相信文明最终战胜野蛮成了人类社会内心确认的信仰坐标。正是有了这一人类终极价值目标的烛照,才使得人类即使多少次与地狱擦肩而过也不至于向地狱边缘坍塌。
现代和哲学关于法的虚拟性设定,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法律的制定运行常常只有一个唯一的真实治世用意。其实,当法治与人治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时,人类社会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冲突。而当法治与人治发生矛盾冲突时,谁服从谁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人类在相当多的历史时间里,不是不懂世间道理,而是为了一己之私、一族之利,一派之益,就是不愿按照实践道路去做,除非人有信仰内制,信守人身盟约,主动压迫自己去遵守人间的规则道理。所以西方睿智者说道,在民主制度下的法治观念上,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应当要获得普遍的服从,但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从立法层面的意义上说,“恶法”不是法,“恶法”当然要受到人们批评和批判,是人们痛斥的对象。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只有良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间法。正是有了这一法的本质约束,中国古代的哲人发出了盛世箴言: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但亦为盛世所不尚,治者不得以而用刑,不过是以杀止杀,刑期于无刑而已。
哲学是一种出自人内心的深层思考,是一种思想和实践相结合的鲜活思考。哲学的源泉来自于人类心灵伸出对自身本能进行思考的需要,它的深层应当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其实人类的理性是不证自明的,
这一理性就体现在人类终极的价值追求在于自由、平等、公平、民主、秩序、文明……崇尚真善美,追求 真善美,鄙视假恶丑、杜绝假恶丑。即使其路漫漫,也得“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哲学与法学的关系,
绝不是一种同位并列在于认识世界,而法律则在于更好地改造世界、管控世界。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被反 复灌输和浇铸这样的观念: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法律仅仅是国家强制力的反映。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型塑的固定概念:法律是不需要讲理的,法学也不需要慧者的哲学思考。正是这一切曾经伤害了人类的法律世界。在智者真善美哲学文明思想的引领下,不断剔除假恶丑野蛮的法学思想成分。即使人间社会发生冲突,即使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有时有着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也能做到如孔夫子所说的“听诉,吾犹人也,必也时无讼矣”。即使往事越千年,在现代也时时考验着人类对自身管理和控制的智慧和能力。其实哲学对法学、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思考目前就是让法学、法律和法律制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轨道,即借助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使得智者与善者相结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有希望,而不是相反。以至于让宇宙星空更加灿烂亮丽,让人类社会更加和谐安详。